 精华热点
精华热点 回忆录《岁月留痕》之:
知青插队,使赵村难忘的日子
一眨眼就是半个世纪。当年的伙伴们大都进入了古稀之年。翻出岁月的过往,重新嚼嚼挺有味道。
伟大人物的一句话,就是我们亿万男女的历史和命运。我们人生的起头,就源于毛主席的号召,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实际这是化解社会麻烦的办法。1966年掀起的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,在中国大地上折腾的昏天暗地。砸烂一切传统最可怕。那惊心动魄的乱局,不感受描述不岀来。后来定性为文化的一场浩劫。我们的少年时代恰恰赶上,亲身经历观摩了这场历史大戏。到1973年,已是第8个年头。大学几乎关门,工厂爬窝,年轻人悠闲的浪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,没什么干的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种地,释放能量,是当时的基本国策。

文.革初期,就有一批大城市的"老三届"开始了插队,如北京,上海等地的年轻人到新疆,内蒙古,黑龙江等边远地区生产建没兵团。到了后期,全国大小城市集聚了更多的失业人口。所以大规模的下乡插队种地也是必由之路。70年代,除了大小城市,连县城中学毕业后的孩子们也作为知识青年到村里了。到农村去,到边疆去,到艰苦的地方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说老实话,不去怎么办,城市养活不起吃闲饭的这批人了。当时说下乡的是知识青年,其实大半是初中毕业的青绿孩子。说知识连少半瓶子也不够,一部分还是未成年人。戴顶知识青年的帽子成了概念。如果放到21世纪重新定义,初中毕业生略比文盲强一档。
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,是在运动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。今日被誉为中华民族伟大的一代脊梁,是因生在困难时期,吃苦受罪,在风雨飘摇中受到了充分的历练,所以有血有肉有灵魂。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,这批人是拓荒者,先行者。
宏大叙事完毕。在这社会的大背景下,小人物的所有戏分都脱离不开时代的舞台。

我们是文.革砸烂教育体系后的首批高中生,偌大的城市只招了4个班的高中生。在榆次城花园路小学,当时小学又办中学,俗称戴帽儿中学。混了两年初中毕业,当时同学的年龄都15岁上下。千年的传统文化被砸烂,读书无用被洗脑为社会一般的认知。到社会上打工赚钱最实惠。我们班上只有2位同学选择了读高中。我是其中之一。
那时找工作无所谓未成年,有的同学一出校门就打工,挣钱就有了自己手头花的。少年是叛逆期,玩儿心大。读书是苦差事,赚钱很诱惑。我犹豫再三。母亲已给我选择了一家央企,说定了去广播录音器材厂上班。人生的十字路口,艰难的抉择。心里还是不甘心,放不下书本。母亲不愿让我荒废学业。最后还是放弃了上工厂就业。
高中班已经开学近两个月了,母亲又托人找到榆次一中领导,插班进去了。在校说混了两年是不过分的。毕业典礼就是散伙会,因为考大学无门。于是乎早早的浪迹江湖。干教师打临工,不到一年,赶上了这波插队下乡的时代浪潮。
1973年10月14日,榆次市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。锣鼓喧天,彩旗飘扬。完后几十辆卡车浩浩荡荡出发,分别把上千的首批插队生送到了各自插队的村庄。
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伙了。插队点是离城不到10里的使赵村。三六九等从来是存在的。使赵村近便条件又好,属于晋中行政公署干部子弟选择的插队点。还有少量来自太原省直机关的子女。第一批14人,带着自己的行李,胸前戴着红花,卡车上体面的梦一样,赶中午就送到了使赵村。

热闹之余,卡车走了。使赵村把我们安顿在生产大队部的院子里住下来,宿舍旁已提前准备了食堂。村里的王春长书记等村干部主持召开了小型的迎接会。吃了顿热气腾腾的接风刀削面。
仪式感完了,该散的散了。回过神来站在院子里,空落落的天空,环望着鸡鸣狗叫的乡村。这才觉得恍如一场梦境。命运的安排,从此的身份是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了。大会上领导喊扎根农村的时候没觉得。仔细一盘算,才感到扎根二字不光是沉甸甸的生僻,更是一块搬不动的命运铁块。这辈子或许就这样子了。好在年轻想的单纯,容易把生活的灰度幻想成浪漫主义的色彩。先好好干吧,走一步说一步。
还好,同批进村插队的还有我的高中同班同桌好友,担任班长的车建军。起码有个伙伴,没有陌生的孤独感。
到年底时,我们使赵插队点陆续从榆次,太原等地来了新伙伴,有近40个同龄男女。晋中地委还安排了一位教育局的干部闫世晶,做我们的带队领导。这伙人同吃同住,还有组织有人管,有烟火气生活化的结构,班集体一般有人给操心。又象一户大人家。锅碗瓢盆齐全,过的是吃喝拉撒的平常日子。起头几个月,我们没有分到各生产小队,由大队统一安排劳动。几十个人的插队生也成立了组织机构,我被选为队长,毛建新等为副队长,晋朝英是团支部书记。
当时正赶上秋收后的初冬,天气寒冷。还记得刚进村的热身劳动。大队给我们安排的头项农活,就是进城掏大粪。给农田准备肥料。哎唷那个哭笑不得。3个人一组的小平车粪车,到城里的公厕去掏粪。不想干硬着头皮也得上啊。拉着车步行十多里进城,掏了大粪装满了车返回来。每天浑身溅的屎尿点子不稀罕。咬着牙一气干了半个月多才熬过去。
那时农业学大寨,战天斗地是精神。冬季农闲本来是天道,但生产大队有上面来的工作组如督战队,白天地里大干,黑了还要开大会。社员们对付不好肚皮但要有革命精神,三九寒天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,而且要一出勤两送饭。早晨6点多钟大队的喇叭就会呜哇呜哇的叫早,7点来钟天擦黑就得上工。

我们是新社员,当年的冬天就在一起集体劳动。40多位知青男女,大冬天被吆喝到西北风呼啸的野地里,拿起钢钎和铁锹干活儿。农田在寒冻季节是没得庄稼种的。不知是哪位缺弦的领导,还是狗屁专家给出的馊主意。所谓农田建设就是找到一块平整的地,上冻前把土堆起来,春天解冻了把土再散开来。听村里的老社员们怨声载道,悄悄的骂说,瞎球闹啊,自古没见过农人做这样的活计,这是放屁脱裤子,白费手续,生硬是闹腾人哩。没办法,领导会上说了,学大寨不是开玩笑,是搞政治,是在闹革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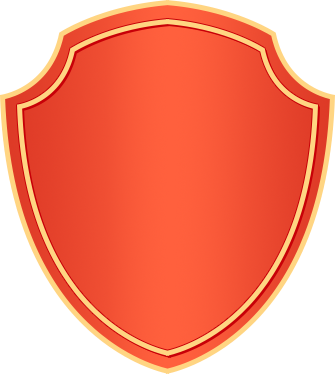
我们在生产大队的院里住了不长时间,就搬到村农机修理厂院内一座老宅子里。据说老宅子没人敢住,曾经风传闹过鬼。我们年轻人群火力旺,不惧鬼神侵扰。简单收拾了一下,40多个男女就搬过来。正房的偏屋留给带队的闫老师住。东西厢房各两间,每个屋里都是通炕,每盘炕上紧挨着睡8、9个人。叽叽喳喳的挺热闹。冬天生的煤泥火热度不够,挤在一起暖和些。年轻男女的心是烂漫的,纯真的色调简单。白天累成个狗,坐在一起胡谝乱侃一顿就来了精神。睡着了也不安神。一天晚上,袁志安在梦中锵锵锵的敲锣打鼓,把满炕的人都惊醒了。他还尽管咧着嘴笑着,敲打喊叫的得劲呢。
四合院老宅里没有南房,东厢房靠南的杂屋间收拾好做了集体做饭的厨房。八队的光棍汉老关给我们做了饮事员。回想来缺油水的三餐,那是很难苦的。早晨玉米面煮疙瘩,高粱面发糕。中午红面汤面,玉米面窝头,晚上小米稀粥,玉米面窝头。每周中午吃一两次白面擀面条,能闻点儿肉腥。不管饭菜怎么难下咽,还是能吃饱。反正男女个个都是大海碗。肚皮规则永远是越穷越吃,越吃越饿。那时我刚过18岁,一天2斤粮食也打不住。最多时上工回来吃早饭,一顿能咥一海碗玉米碴,6个窝头。中午两大碗面条。晚上吃饭前肚子又饿的咕噜咕噜的嚷叫了。
那阵子农业学大寨不是生产是运动。许多地方作戏作秀。比如说上工红旗飘飘,出工不出力应付检查摆排是常有的事情。有的地方还闹夭娥子,组织大批社员把马路两旁的杂草拔掉,今天想起来仍哭笑不得。

我们插队生顶着三九严寒,在大队安排的南村口农田堆土。地皮在最冷时冻的有近半尺多厚。劳动工具有大锤,钢钎,铁锹,小平车运输。刺骨的北风呼啸,这倒是治懒人的天气。不动就会冻的手脚麻木。早晨天还没大亮,我们就上土了。劳动的地方离我们居住的院子也就不到2百米。按照大队部的要求,社员的早饭和午饭都要集中起来派专人送到地头。就着西北风吃饭,好多人的胃口顶不住刺痛,我也经常难受的不行。有一天遇上西伯利亚过来的降温寒潮,风特别大。到了中午饭时,我是插队生的队长,就擅自作了主。老子不弄那个形式主义了,反正不误工。于是擅自决定让大家用几分钟回了食堂,吃了饭赶紧的回来继续干。结果当天有报告员汇报给市乡派来的工作组。工作组找我谈话警告,这种行为性质严重,这样做就上升为破坏学大寨的政治了。我的娘,吓的我出了一身冷汗。再也不敢造次了。
都是爹生的娘养的,城里长大也没干过多的体力活。那个时代穷,吃的都紧张,人哄地皮,地哄肚皮。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没给农村带来什么变化。那个年代走哪儿也没娇生惯养的条件。就是活在吃供应粮的城市,每天也得擦煤泥,水站挑水,掏炉渣打泥糕的家务活儿。我们插队点上还有若干从京城省城来的省级厅级大领导的子弟。聊起家庭生活,差距也没多大。就是吃的细粮和肉腥比我们多些,饭里可以敞开倒酱油调剂味觉。穿衣打扮更无大的区别。到了一起,谁也无任何特殊的待遇。同样一出勤两送饭,什么罪什么苦都得扛下来。印象深的有我的好友胡明亮,当时瘦弱的很。女同学贾岷沙都是高干子弟,性格洒脱活泼,同是一日三餐扛着大海碗。我倒是属于饭量大的,他们的食量比我还猛。
千金难买少年苦。人有享不了的福,但没有受不了的苦。不管后来如何评说这段历史,如何说三道四,该不该下乡插队那是题外话了。反正城里的年轻人自小没吃过大的苦头。本应是读书学习的黄金岁月。到农村算是受了罪。但意外的效果是强健了体魄,锻炼了意志。一群人中没有面包男,娘娘腔,个个行的直站的稳。历练对人的成长成熟好处多多。经过了与大地的磨擦,风雨中的摔打,这一代人还真成了民族振兴的脊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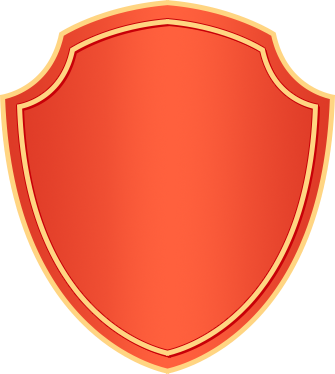
到村里的头一个冬天很难熬。白天一出勤两送饭,直盼到太阳西下天擦了黑,个个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了窝。晚饭后稍一停歇,到底还是年轻,宿舍里就叽叽喳喳又说又笑起来。那阵子没有电视,手机更遥远。混在一起娱乐,就靠扑克牌热闹,喜安静的二人对奕象棋。一个十多平米的屋里住8、9人,一进门就上炕。卫生条件自然差,放屁打嗝脚汗臭,这些都不在话下。对面4间厢房住满了人,院子也不大,隔音效果不好。半夜三更都睡熟了,也是梦话梦境交响乐。娇情的人也得适应这种环境的。每间屋都象蛤蟆窝里搅棍子,充满了朝气,乱的头疼。年轻男女的心思简单,再苦累但笑声是脆的。
一样的生活环境,不同的心志。使赵村是乡政府所在地,是有3千多人口的大村子。村里有的历史文化故事,人才济济。白天战天斗地,晚上大队还组织了宣传队,集中了几十个文艺人才排节目,好在正月里上戏场给社员们演出。我们这伙城里来的俊男靓女,也有歌舞器乐的爱好者。刘晓燕,王世贤,高小冬,孙小青,建潮,小保儿等参加了村里的文艺宣传队。白天劳动,晚上还参加节目排练。乐呵呵的不知疲劳。

值得一提的我们使赵插队点,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学习氛围。这得感谢来自大城市高干家庭的几个插友。他们的确有不一般的家庭教养,见识就是长远。人性从来是主动的少,被动的多,倦怠的是主流。在圈子里受的感染影响了我的一生。北京军区子弟储海林,省里来的明亮,永健,玉康,还有我的老班长车建军,他们都很爱读书。海林,明亮更有格局思维,他们不管农活多繁忙多苦累,一大早起来就学习英语900句。脚踩在使赵村的地头,心中却有踏海过洋的雄心。闲时坐在一起,谈时事变局,充满着对人生的期待和美好的向往。友人的行为启迪也深深触动着我。获益良多。我们当时的年令处在青春苦闷期,站在人生选择的重要关口。自小我有初心喜爱文学,所以在闲暇时间看了大量的书籍。起码没有沉沦在世俗中荒废。
活了一辈子已充分的验证,每个人的自我设计自觉的追求就是因果。特别是少年时尤为重要。我们这伙人到了晚年已有明确的结局。明亮后来上了大学,又到漂亮国留学,成了博士教授。海林也是大学教授。个人的努力成功了自己。有一种现象,当年我们在插队时努力学习进取的,后来即使分配到厂矿企业,后来个人的发展也不错。到体制内工作的,走上社会管理岗位的。起码比随波逐流活着的结果好的多。老年后更有明显区别。领着丰厚退休金的比领着一般的退休工薪,差距不小。
进村后几个月,第二年春天,考虑到我们的生计着落,40多插队生进行了分队安排。使赵村当年有8个生产队,从北到南依次是1队到8队。我和吴新光,岷沙,小冬等分到了村东南头的第8队。从此,我们吃住仍旧都在一起,但农活安排随了各自的生产队。分工有了变化。晋朝英有学医的经历,做了村里的赤脚医生。胡老大亦农,建新因体魄高大有力,分配去了磨坊劳动。先慧到了大队研究灭虫害的科研组。
我分到了第8队,还很庆幸。记时当时的生产队长叫王德会。王队长性情粗囟,8队社员开大会,他一边靠在桌边哇啦哇啦讲话,一边不停地从身上捉虱子,然后当众用拇指甲把虱虫血杀在桌面上,逗的男女哈哈大笑。老王人粗心不粗,领导生产可有一套。当年秋收决算下来,还是村里的丰收先进队。我那年挣了4百多工分,除了各项粮菜款的扣除,年底还领到了1百多块的现金分红。
都是20上下的年龄,正是爱情的季节。放到现在,那浪漫早泛滥成灾了。说不定会生产出一批后一代。可是那时代爱情是不开放的。男女恋情的私约密会认定是资产阶级的一套。有爱慕的表答也象贼一样,仿佛是搞流氓黄色活动。所以我们2年里很安静。大家紧张劳动的也没多闲空,连胡思乱想的时间都挤不出多少。
下8队干了一年。秋收过后,大队领导找我谈话,决定把我从生产队里抽出来,调到村小学担任5年级的教师。幸好我有过在城里做教师的经历。自然不怵,得心应手。
于是从体力劳动者到了学校,脱离了风吹日晒的大田,到学校整干了1年的教书匠。直到插队两年期满后招工回了城,到位于太谷的军工企业753厂当了工人。

使赵村插队2年,正是人生的华年,风里雨里的折腾,有的是不可磨灭的记忆,更留下走向成熟的印痕。当初是奔着扎根口号来的,结果是镀了层金皮跑了。两年感觉是游戏一般,灵魂还没定神,眨眼间就游移到另外一个天地。
离开使赵时五味杂陈,留恋难舍,心里涩涩的不忍。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同学,一炕睡岀来的亲热,那种锅里碗里碰撞出来的感情。这是今生永远抹不去的印记。天下没不散的宴席。就这样分手了。多年来心里还十分惦念在村里相处熟惯的那些好人们。村领导王书记,志强,马二担,对我们插队生倾注了许多关爱的康月喜大叔,食堂做饭的老关师傅,明远大哥等。还有当时村上才华出众的马家兄弟,仲业,胜英,亚明等,都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那一幕幕美好相处的经历回放,仍旧历历在目。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