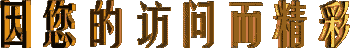精华热点
精华热点 
作者尹玉峰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
长篇诗境小说《野姜花》
连载二十三
作者:尹玉峰(北京)
晨光切开苹果枝,赵泼儿
站在画架前,她睫毛颤动
像蝴蝶撞进心
林松岭的笔尖
混着松节油的香,落在
画纸上,洇开一片希望
1
夏日的晨光像一把细刀,从土坯房的窗缝斜劈进来,刺得赵泼儿猛地从炕上弹起。她摸向肚子的手停在半空——那里仍平坦如初,却像揣着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。
“苹果啊,快红吧……”她喃喃重复着梦里的话,舌尖仿佛还残留着那种酸涩的味道。窗外,父亲赵驼子的斧头正“咔嚓咔嚓”地啃着木头,每一声都像劈在她心口。
走到院子舀水洗脸时,一股酸水突然涌上喉咙。赵泼儿弯腰干呕,再抬头时,正撞上父亲阴鸷的目光。
“赶紧嫁了吧。”赵驼子把斧头楔进木墩,声音比斧刃还冷。
水瓢从赵泼儿手里滑落,在青石板上砸出清脆的响声。“嫁谁?”她明知故问,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。
“臭头啊!”赵驼子啐了一口,“他媳妇跟人跑了,正好缺个暖被窝的。你这样的……”他上下打量着女儿,“有人要就不错了。”
“不嫁!”赵泼儿猛地抬头,眼睛里燃着火。她想起城里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,说好等她怀孕就结婚,结果连出租屋都连夜搬空了。
赵驼子突然抄起斧头走过来,赵泼儿下意识护住肚子后退两步。“你在城里干的那些烂事,说梦话都吐干净了!”他压低声音,却像闷雷滚过,“那王八蛋早把你耍了,你还想挺着大肚子赌一把?”
院墙外传来脚步声,赵驼子立刻换上笑脸朝路过的村民点头,转身时脸色又阴沉下来:“丢人现眼!让我的老脸往哪儿搁?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响,最后突然咆哮起来:“你去死——我们老赵家没有你这个现世报!”
赵泼儿像被雷击中般僵在原地。父亲的话在她耳边炸开,和梦里黑头白身的虫子一起钻进她的脑子。
晌午的果园里,国光苹果挂满枝头,青涩的果实裹着层白霜。林松岭支着画架,笔尖在宣纸上晕染开一片青绿。他画得很专注,连身后窸窣的脚步声都没听见。
突然一双带着花草香气的手捂住了他的眼睛。“云秀!”林松岭脱口而出,立刻感到捂住他的手僵住了。
“真没劲!”赵泼儿甩开手,嘴唇抿得发白。她今天特意换了件水红色衬衫,头发也用火钳烫了卷,可现在全成了笑话。
林松岭尴尬地清了清嗓子,继续调他的颜料。赵泼儿盯着他修长的手指看了会儿,突然说:“我跟你谈点正事行吗?”
见林松岭抬头,她急忙补充:“关于云秀的。”这句话果然让林松岭放下了画笔。
“她犯小人了,”赵泼儿压低声音,“是张红和齐老师。”她看见林松岭的眉头猛地跳了一下,知道自己押对了宝,“最开始…他们还让我当枪使…”
林松岭“啪”地合上颜料盒,画架都来不及收就要走。赵泼儿一把拽住他的袖子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:“我想认错都不行吗?”
“松手。你找云秀认错去!”林松岭甩开她,头也不回地往果园外走。他听见身后传来抽泣声,然后是赵泼儿歇斯底里的喊叫:“我就这么招人嫌吗?丢人现眼!我是现世报啊——”
画家加快脚步,直到风中飘来刺鼻的农药味,他回头时,看见赵泼儿正启开一瓶乐果。
林松岭像阵旋风般折返回来,军绿色衬衫下摆被急促的动作带起,露出腰间一截皮带。他劈手夺过农药瓶时,玻璃瓶溢出琥珀色的液体,在阳光下折射出危险的虹光。
“坐下!别动!”他声色俱厉地喝道,顺手将瓶子抛向远处的灌木丛。惊起的山雀扑棱棱飞过赵泼儿头顶,几片羽毛落在她凌乱的发间。
赵泼儿突然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:“别管我!我这身子…我这脸…”她揪着水红色衬衫的前襟,布料在指间皱成绝望的漩涡,“早被城里人糟践透了!”指甲透过衣料在胸口的皮肤上抓出血痕。
林松岭深深叹了口气。他注意到赵泼儿脚上那双过时的塑料凉鞋——左脚带子断了,用烧红的铁片勉强粘合,和城里姑娘们穿的细带皮凉鞋天差地别。林松岭突然单膝跪地,从帆布包里抽出速写本,铅笔在纸面上敲出笃笃的节奏。
“我命令你坐下来。”他语气缓和下来,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,“有什么委屈,你边说,我边给你画张像。”铅笔尖在晨光里闪了闪,“就画…你第一次去城里时的模样。”
这句话像按下了某个开关。赵泼儿浑身一颤,泪水冲刷着廉价脂粉,在脸上冲出沟壑。她缓缓跌坐在树桩上,身后是挂满青果的枝桠。一阵热风掠过果园,树叶沙沙作响,晃动的光斑在她身上流淌。阳光透过叶隙,在她散乱的梨花头上跳跃,泪眼里碎光粼粼,像打翻的汞珠。
林松岭的铅笔在纸上游走时,一片槐树叶子突然落在画纸上。赵泼儿下意识伸手去拂,指尖却不小心划过画家手腕内侧的疤痕。两人同时一颤——她的指甲缝里还沾着除草时的泥土,他腕间还留着颜料的味道。
“别动。”林松岭突然抓住她欲缩回的手腕,拇指无意识摩挲过她突出的腕骨,“你这里…”他蘸了点赭石色颜料,轻轻点在她手腕青筋的位置,“有根血管跳得特别生动。”
赵泼儿屏住呼吸。她闻到画家身上松节油的味道混着汗水的咸涩,看见他睫毛在阳光下投下的阴影正在微微颤动。当笔尖触及皮肤时,她错觉那点凉意会顺着血管流进心里。
2
远处传来云功德带领村民开山的声响,铁钎凿击岩石的叮当声里,赵泼儿突然轻声说:“松岭哥,我…我是不是真的很坏?”
林松岭的笔尖顿了顿,随即在画纸上添了一笔:“你只是被生活逼到了墙角。”他抬头,目光温和而坚定,“但墙角也有野姜花,开得比谁都热烈。”
赵泼儿的眼泪又涌了出来,这次却是带着笑的。她望着画纸上那个青涩的少女,突然觉得,或许…她真的还能重新活一次。
远处的开山声忽然停了,山谷里回荡着最后的钎子回声,那声音像是从大地深处挤出的叹息,渐渐消散在风里。林松岭趁机压低声音,手指轻轻点向赵泼儿身后一株野百合。那花苞才刚裂开一条缝,露出里面嫩黄的花蕊,比周围的晚了整整半个月,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有些倔强。"你看那迟开的山花,"他的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,"等秋霜打过,结的籽最饱满。"
赵泼儿的哭声戛然而止,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捂住。她顺着画笔的方向望去,看见阳光透过百合花瓣,在地上投下淡青色的影子,那影子随着微风轻轻摇曳,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一只金龟子正费力地爬上花茎,翅膀壳上还沾着露水,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,像是背着一整个世界的重量。
"这是我父亲的人生感悟,"林松岭突然换了语调,手指无意识地摸向胸前口袋里露出半截的老照片。照片边缘已经发黄,被岁月啃噬出细小的缺口,隐约可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抱着吉他,他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,眼神里却藏着说不出的坚韧。"他还谱了曲。"林松岭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怀念,像是在回忆某个温暖的午后。
"你父亲?"赵泼儿的声音突然清晰起来,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她看见林松岭骨节分明的手指在微微发抖——那双手既能画出价值连城的国画,也能在寒冬里帮父亲推三轮车卖烤地瓜。那双手布满了细小的疤痕和茧子,像是刻满了生活的痕迹。
林松岭的喉结滚动了一下,像是咽下了什么。他翻开画板夹层,取出一盘老式磁带,塑料外壳上还用褪色的红漆笔写着"岭儿大学学费——1989.8"。那字迹已经模糊不清,像是被时间冲刷过的记忆。"老爸下乡时被镰刀割断过脚筋,"他的拇指抚过磁带上的划痕,那划痕像是他父亲生命中的伤痕,"下岗后每天扛两百斤面粉,就为让我妈能继续吃药。"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,像是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。
林松岭的声音忽然低沉下来,像深秋的山涧流水,带着一丝凉意。"要说苦难..."他的拇指轻轻抚过画板上那道凹痕,仿佛在触摸父亲粗糙的手掌,那手掌上布满了老茧和伤痕,"为了生存,爸爸自谋职业开个小餐馆,却被黑社会砸了,他们用砍刀,砍断了爸爸的腿..."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,像是在回忆某个痛苦的瞬间。
赵泼儿的瞳孔骤然紧缩,像是被什么刺痛了。她手中的野花茎"啪"地折断,汁液溅在她发颤的手背上,那汁液带着一丝苦涩的味道。她猛地捂住嘴,指缝间漏出半声惊喘,像是被人当胸捶了一拳,整个人都僵住了。
"砍...砍断?"她的声音变了调,像砂纸磨过粗粝的树皮,带着一丝难以置信。突然,她抓住林松岭的手腕,力道大得惊人,指甲几乎陷进他的皮肉里。她的嘴唇颤抖着,却发不出完整的音节,只有滚烫的眼泪砸在两人交叠的手上,那眼泪带着一丝咸味,像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悲伤。
"我上小学时..."林松岭突然笑了,眼角挤出细纹,像是岁月刻下的痕迹。"父亲用松木做了副高跷,绑在断腿上。"他比划着高度,"再套上那时流行的喇叭裤,走起路来..."他模仿着那种不自然的步伐,却突然停住,因为看见赵泼儿的眼泪正大颗大颗地砸在泥土上,溅起细小的尘埃,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
林松岭提高声音:"我上大学那年,爸爸坐在轮椅上,在人民广场弹吉他。"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——一个消瘦的男人坐在轮椅上弹唱,断腿处绑着自制的话筒架,面前摆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罐。那罐子里装着一些零钱,像是他父亲一生的积蓄。
"六弦琴,你轻轻地唱..."林松岭轻声哼唱起来,歌声惊飞了树梢上的麻雀,那些麻雀扑棱着翅膀,消失在远方的天空里。赵泼儿看见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:"今天被城管赶了三次,但赚够了岭儿半个月生活费。"那字迹已经模糊不清,像是被时间冲刷过的记忆。
"世界上..."赵泼儿的声音轻得像片落叶,她收回手,不自觉地摸向小腹,那里藏着一个小小的生命,像是她和林松岭爱情的结晶。"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父亲..."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,像是在呼唤着什么。
3
林松岭突然用画笔蘸了朱砂红,在画纸上重重一抹,那颜料在纸上晕开,像一簇跳动的火焰,带着一丝炽热。"他不是特例!"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,"千千万万的工人..."他的笔锋转向,勾勒出一个弯腰劳作的背影,那背影在夕阳下显得有些孤独,"都是用这样的脊梁..."又添上几笔,变成扛着钢钎的云校长,那钢钎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,"撑起了这个时代!"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豪,像是在歌颂着什么。
赵泼儿突然蹲下身,抓起一把泥土在掌心揉搓,细碎的沙粒从她指缝间簌簌落下,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"我真心佩服你老爸,"她的声音闷闷的,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,"更佩服你。"一粒砂砾粘在她湿润的睫毛上,在阳光下闪着微光,像是她眼中的泪光。
林松岭看见她手背上有一道新鲜的擦伤,渗出的血珠混着泥土,凝成暗红色的痂。那是刚才她慌乱中撞翻画架时留下的。那痂像是她生命中的伤痕,带着一丝疼痛。
"云秀那天..."赵泼儿突然抬头,眼神里带着一丝迷茫。"你只是..."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模仿着林松岭当时踢球的动作,"把球轻轻推到云秀脚边,就像..."她顿了顿,从口袋里摸出个褪色的布口袋,里面装着几颗水果糖,那糖的包装已经有些破旧,像是被时间遗忘的糖果。"就像我妈活着时,总把最甜的糖留给我。"接着,赵泼儿幽幽地说,"你是好人!"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真诚,像是在表达着什么。
林松岭朗声笑起来,笑声惊飞了草丛里的蚂蚱,那些蚂蚱扑棱着翅膀,消失在远方的草丛里。他弯腰捡起滚落在地的桔子,在裤腿上擦了擦,那桔子皮裂开的瞬间,清甜的香气弥漫开来,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"我是好人不假。"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嘲,"你也不是坏人啊!"赵泼儿咯咯笑了起来:"我要是坏人的话,世界上还会有好人吗?"她歪着头,鬓角的碎发被汗水黏在脸颊上,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
一阵裹挟着野蔷薇香气的山风突然袭来,吹散了赵泼儿鬓角的碎发。林松岭自然而然地伸手,却在即将触及时突然转向,假装去扶摇晃的画架。他的指尖在空气中划出看不见的弧线,最终只是递过去一块叠得方正的蓝格子手帕。那手帕上带着一丝淡淡的香气,像是他生命中的温暖。
"擦擦。"他别过脸去看远处的果园,那果园里结满了果实,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"你脸上有..."话音戛然而止,因为赵泼儿正用那块手帕按在眼皮上,泪水很快洇透了棉布,晕开一片深蓝色,像暮色中的山影,带着一丝忧伤。
赵泼儿忽然轻声一叹:"人与人之间..."她的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吹散,目光却灼灼地盯着林松岭,"怎样可以建立起更加良好更加稳定的关系? "一片落叶打着旋儿落在她肩头,又滑落到地上,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
"真诚!"林松岭弯腰捡起那片叶子,叶脉在他掌心清晰可见,像是他生命中的脉络。"除了自己首先做到..."他的拇指轻轻抚过叶缘的锯齿,突然笑了,"还是自己首先做到。"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坚定,像是在表达着什么。
赵泼儿的表情瞬间凝固,像是被什么定住了。"什么意思?"她的声音陡然而起,带着一丝疑惑,像是在追问着什么,惊飞了树梢的麻雀,"觉得我不够真诚?"
林松岭摇摇头,从画夹里抽出一张素描:"记得那天吗?"画上是赵泼儿蹲在田埂边,小心翼翼地为受伤的小狗包扎伤口的样子。"真诚就像..."他的笔尖在画上点了点,"云校长凿石开道的执着,云秀老师深夜里给学生批改作业的灯光,村支书把自家最后半袋面粉送给孤寡老人..."
"那臭头呢?"赵泼儿突然打断他,眼睛却盯着画中的自己。她的指尖轻轻擦过画纸,留下一点汗渍。
林松岭的声音忽然低沉下来,"云秀老师跟我说过,臭头跳进冰窟窿救起落水的孩子,自己冻得嘴唇发紫,却悄悄躲开了记者的采访。"
赵泼儿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。"这些年..."她的声音哽咽,":这些年我尽遇到坏人,早点儿认识你就好了..."
【版权所有】待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