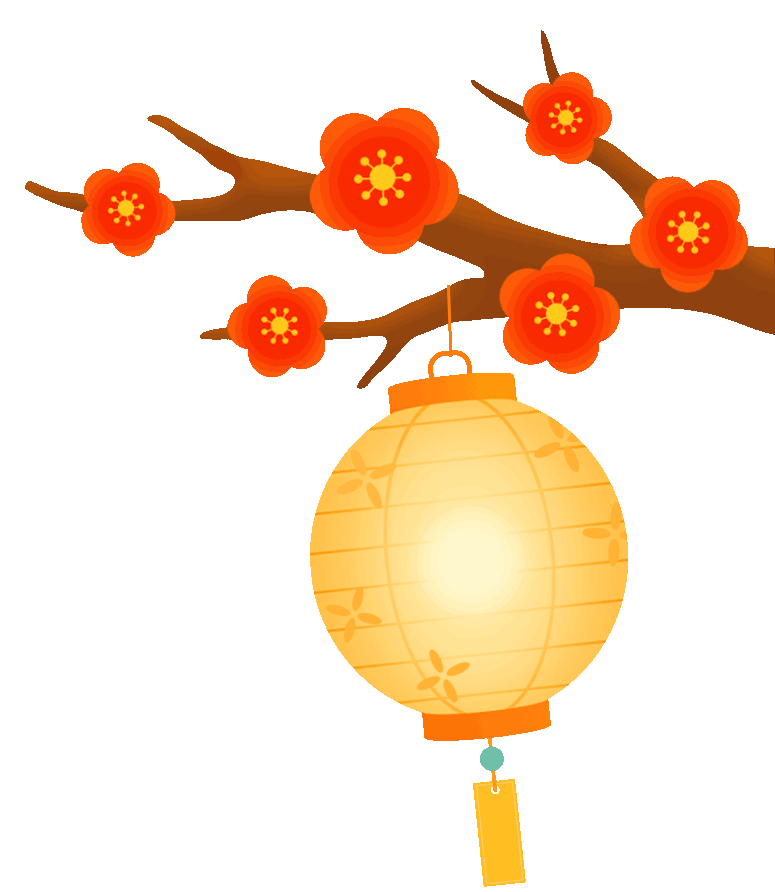打牌 (散文)
◎陈平骊
前数日临时有事去一朋友家。是晚饭后,见客厅云烟幢幢,两男客正吞云吐雾,和另外两女,四人凑成一桌,目不旁视,在干中国人都知道干的事。如果这时有愚笨者看到这儿不明所以问我:他们干什么咧?我一定回嗔一句:你是中国人吗?
人是有不同存在方式的。就我所见,对于很多人而言,工作之外,其存在方式,就是打牌。
打牌者,打麻将也。这是中国人从明代以来最乐此不疲的爱好,古称“叶子戏”。《红楼梦》里面就描写有贾母和贵妇们作乐打牌的情景,成为中国著名民俗之一。而现在牌风之甚,好像尤以南方城镇居多。任何事物的存在或者发展,自有其理由。先贤说:不为无聊之事,何以谴有涯之生?怎样打发时间呀,怎样避开寂寞呀!人是群居动物,最怕独自面对自己,所以四人一组,有趣而又莫测的麻将游戏,自明代开始就流传至今,并有愈演愈烈之势,被誉为国粹实不为过。
从我住家一边窗台望下去,是对面一栋楼的二楼大平台。那儿从来是热闹和市井的。除了冬天和春天,有鸟儿飞来停歇在细雨朦胧的水泥地面,散步或发呆,雀跃又飞走,其他两个季节,尤以夏天为最,总盘踞着一张方桌,有数个老太太老头凉棚下围坐打牌,惯常是无声地,但突然就会吵闹起来,忒大年纪的人,为一张牌的花招,争得面红耳赤。这些对我而言都是可忍受的。 我闲暇时的存在方式是不爱出门,操持完家务,有自己的时间,最常干的就是猫一般盘踞沙发,看书或者随意写点东西,或者听音乐、独坐,无由陷入沉思默想,窗外的声浪常常就会干扰我的存在方式,因而也不喜欢开窗打开窗帘。然而久了,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夏天,比如现在或类似现在这样的时辰和季节,大平台就会出现临时牵扯的电线,擎上灯泡,准备晚饭后,南风徐来,几个麻友挑灯夜战。这样的麻将会,只要天气晴朗无雨,往往从黄昏开始,直至半夜。记得大前年的麻将会尤其红火,持续整个夏天,尤其半夜,让我不胜其扰。晚上看书看电视或上网,我都能像老尼入定般,视若等闲,不受其干扰,但到了夜半,必须上床了,熄灯后,那灯火幢幢,魔影般动荡着便投影到我住家的窗帘上,让我无端惴惴不安。我睡眠十分不好,窸窸窣窣的麻将声声声入耳,就是难以入眠。更可怕者,是有时突如其来战事的开端。不知所以地,就开始了麻将吵架的汉腔大歌剧。我曾央求在商场做事的一熟人,给我弄到海绵耳塞,想堵塞那些滚滚扑来的花腔男女高音,但收效甚微。汉腔歌剧往往鼓之以雷霆,煞之以风雨,忽如炸雷,继以迅雨。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一男一女好像为谁毁牌吵架,男声好似“一八一二序曲”中的“马赛曲”,启动激昂雄伟,终究灰飞烟灭;而女声则如拉威尔“波莱罗”中,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主题,因固执和坚持,由开端的涓涓溪流而至奔腾澎湃,最后统领一切。男的竟然斗不过女的。失眠中干脆自嘲的想,听这样有趣的市井吵闹,男女斗嘴,也不失为一桩趣事。甚至有时幽默的想,若窗外是那细流渐至雄壮、终达高潮的声浪,窗内有人在按着节拍和旋律行夫妻庄严圣事,是什么感觉呢?比一边听音乐看电视一边行房事的效果如何?道貌岸然者,此句可蒙着眼睛不看也。
类似夏夜平台的今夜无人入眠,这两年倒是好多了。或是有义愤填膺者举报扰邻,芳邻不得已而偃旗息鼓。偶尔或有一举,更多时候估计是转入了室内。清净之余,却不免有所悟:那些该让你看到或听到的故事,一定会送到你的眼前或耳边,你想避都避不开。我想,任何偶然都是富有意味的。我们既非名流大腕,阅人事无数,也非惯常以主动寻觅刺探他人秘事为业的方舟子之流,在我们一生当中,耳闻目睹的事实在有限,那么有限进入我们知觉范围内的事情,每一个相逢并相识的人,每一件发生并影响你的事,必然有其含义。
记得以前春节回家乡探亲,年三十前,大街上熙来攘往,人们忙着采办年货,确实具有忙年的闹热红尘气息。奇怪的是,一到正月初一开始,大街上除了静默的天空一片惨白,飘飞着稀薄的太阳或者雪花,偶尔可见三五成群的孩子干什么鬼祟勾当围在一起,然后捂起耳朵忽的跑开,停顿的一瞬,便听见突然一声或连续的爆响,除了这点耐人寻味的自然或人事景致,正月年假的街道和城镇,是可用以萧条和寂寞来形容的。但只要你有心,上一溜老街走上一趟,而且你耳朵不聋,你就会听见:两侧家家紧闭的门窗内,传来人们都心照不宣会心一笑的特有声音。窸窸窣窣的、稀里哗啦的,欢快愉悦的,那便是麻将重新洗牌的独有旋律了。
不知从何时开始,中国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或是团队,发明了让老外不懂的自动麻将桌。据说这自动麻将桌,已被推举为当今中国四大发明之一。另外三大发明是什么,孤陋寡闻如我,却不甚了了。然私下暗忖,其调侃的味道大概也和麻将桌不相上下。所谓自动者,就是免去了大家洗牌的麻烦,让自动桌代劳,一牌胡了,自动桌暗箱操作,将洗牌、码牌瞬间全部搞定。我们自古以来都是聪明智慧的民族,从发明自动麻将桌可见一斑。
让我想想,第一次见到这种神奇的自动桌,是若干年前春节回家乡,和哥嫂团聚时有幸目睹。兄嫂见我惊异,都觉好笑。观赏一遍方敢开口问,才知这种桌子已流行大江南北、遍地开花了。
兄嫂知我不会打牌,总让我行成人观礼仪式。但以前他们曾如此这般的努力过。让我上桌,妄图教会是所谓高知阶层的妹妹。可惜,有限几次的上桌经历,总让兄嫂们急得跳脚,或者气得无语。先还耐心地言传身教,最终无奈放弃,总结为孺子不可教也。我确实一见那些规规矩矩但又千变万化的牌码,就眼花缭乱,呆若木鸡。或者抓耳挠腮,瞪着大眼发呆发怔是最经常的表情。那时刻大哥最著名的名言就会放出来:我们大家都去睡一觉吧。呵呵,或者,大嫂虚伪的笑着环视大家附和:我们去逛一遍商场怎么样……就这样,有限几次的上桌经历,最终在大家一致的攻讦挖苦中,彻底结束其短促惨淡的历史。然而我倒很不在乎。孺子不可教怎么了?不会打麻将怎么了?不让我进地球么?不让我做中国人么?不让我生孩子么?不让我教书么?最后我每每怡然自得的行成人观礼,或怡然自得的一旁看书发短信。亲友们也怡然自得打牌,视我为空气了。
然而,让我无法怡然自得的是,春节的年景已变得和小时候大不一样。小时候过年一定是最彻底的人情演出,或者是面子人情的大汇演。一年到头不见面的七大姑八大姨,曲里拐弯的远房亲戚,都会在初一初二最迟初三,纷纷冒出,打一个千,拜一声年,道一声扰,接一根烟,然后面带完成任务的微笑离去,继续其流水作业。那是一种成为习惯、而不知改变的中国世俗社会的表面人情,虽然表面,也有一种人情味在。不知从何时开始,可爱又可憎的年味变化许多,其中之一,大家都用手机拜年了,然后心照不宣,借年宴或团聚的机会,关起门来共同玩弄小小的136张牌码。这已成为中国南方、保守说中国湖北地区,过年最常见的景象。这样的景象我想一定会按照其惯性,泰然的存在下去。只要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和人情习性不改变,麻将及其麻将桌上的风景,就会上演到无穷尽头。
作为一个人,我隔岸观景也好,自我固守也好,都是一种存在方式。就像麻将有其事实胜于雄辩的存在理由一样。我不知孰好孰坏,也不想判断哪一种消遣的存在方式更适合上帝的意旨。时光永在流逝,而中国人的生活风景常常是新旧杂陈,百味莫辨。无论新旧,都同样真实,同样令人黯然魂销。
陈平骊,网名念荷、号晴窗初雪。
大学教师,两栖诗人。中华诗词学会、中华辞赋社、湖北省作协、湖北诗词学会会员。诗文散见全国各媒体刊物并入选各诗歌选本。数次获得全国诗词大赛金奖、一等奖。
出版旧体诗词集《晴窗集》《雪渡集》,新诗集《时间的河岸》《花冠》,散文集《上帝的窗子》等。

举报
 精华热点
精华热点